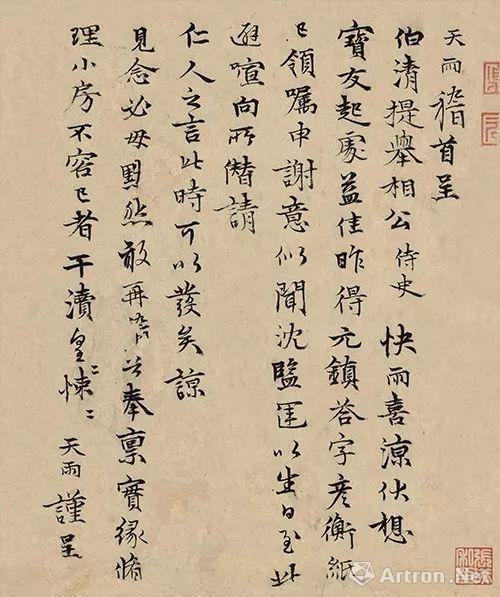南龛石刻的历史光辉
李雪梅
漫步于南龛石窟,放眼望去,或许你会惊叹于南龛摩崖造像的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色彩之艳丽。然而,当你沿着石壁轻轻触摸那些或隐或现的题刻、题记时,也许你更能感受到那份扑面而来的千年巴州古朴厚重的文化气息。一代代文人墨客、一届届官府政要,似乎正沿着龛龛题刻向我们悄然走来;一段段风流佳话、一片片肺腑真情似乎正透过斑驳的石花向我们娓娓道来。
南龛石刻主要由造像、造像记、装彩记、修缮记、题名表、艺术字及大量的诗词歌赋组成,如一部刻在崖壁上的史书,为我们逐一解读那些尘封的往事;又似一幅浓墨重彩的壮美画卷为我们展现那千年古寺的奇容秀貌。南龛石刻是史、是诗,是景、更是画!
唐肃宗时期的高级官员谏议大夫严武因房琯事件,在公元758年被贬到巴州担任刺史,于严武个人而言,的确是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波折,可是,于巴州而言,严武的到来可以说是将南龛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寥寥两百余字的《严武奏表碑》犹如刻在云屏石上的光荣榜,它向我们讲述了这座古寺得以“福地重光”的历程:当初来巴州的严武在南龛的荆棘之中发现这些始建于前朝的古佛龛时,为其造像艺术深深感染,不仅在此建房宇、移洪钟,对寺庙进行精心修葺,还上书皇帝为寺庙求得了“光福寺”的赐名。从此,光福寺“满园清辉、岚浮翠微”,“焚香无时、燃灯不夜”,一下成了无数文人墨客和香客信众的精神家园,“光福寺”寺名也被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没有唐时之严武,就没有今日之南龛。翻开巴州的历史,年仅30出头的严武在巴为官期间,不仅“颇有政声”,也极具文学天赋,为巴州宗教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离任巴州后,后人还专门在城门西边立“去思碑”以示纪念。
在唐代,严武、史俊在崖壁上留下《题光福寺楠木诗》和《寄严侍御楠木诗》,分别以“临溪插石盘老根,苔色青苍山水痕”、“结根幽壑不知岁,耸干摩天凡几寻”赞美楠木树的古老壮观;刺史署长史韩济在严武为报答对朝廷有功烈父亲中书侍郎严挺之而捐资开凿的观音像旁为其题写造像题记,称赞严武是“於铄史君,孝心不忘”;诗圣杜甫因好友严武在巴为官,也常与严武在南龛游玩作诗,在老君洞崖壁上留下了著名的《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既赞美楠木树“孙枝长丈许,老干未肯仆。昔年重九日,来者必三顾”的古老壮观,又讴歌南龛古寺的宁静祥和有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它在诗中善意提醒后人“他时倘再来,莫指桃园误”;贬谪官员羊士谔也因感于严武对光福寺的贡献而在崖壁留下《题南山光福寺》,“传闻黄阁守,兹地赋长沙。少壮称时杰,功名惜岁华”,盛赞严武之才堪比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由此可见,南龛崖壁上的唐代题刻都与严武有着极大渊源。
在宋代,留在南龛崖壁上的题刻以诗词为主。那些做官巴州的州官结伴而来,他们在南龛饮酒、赏景、赋诗,以寄托自己对南龛这片圣地的仰慕之意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宋代一位巴州太守在秋高气爽之际,来南龛登高行乐,摆酒设宴、谈论古今,他们“倚虚壁、临绝巘、上层楼”,到了黄昏仍不愿归去,临行前还要在洞内留下《水调歌头》让我们后人去回味他们那份“坐上尽佳客,一醉破千忧”的风流与洒脱、去揣测他们那份客居他乡的无奈与愁思;南宋的巴州刺史杨概也选择了在南龛福地的山门石上雕刻观音造像,并于父亲忌日在造像旁题赞:“谓此是观音,初因匠石镌。谓此非观音,形象已俨然。”以此赞美匠师精湛的雕塑艺术;又以“人谁无父母,是山孰比坚。稽首净圣王,与山千万年”展现他恪守孝道、感恩父母,希望父亲能够与观音菩萨一起像山一样在心中千万年永存。
在南龛的崖壁上,鲜有元、明两代的痕迹。从这两个朝代的历史来看,蒙古族统一中原建立元朝的时间较短,作为在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他们对汉文化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当朝统治者甚至还对汉文化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禁锢,所以文化氛围相比其他朝代也明显逊色得多;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依靠明教而建立明朝,后来却又因害怕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而禁止了一切教派活动,对各教徒进行大肆屠杀,可以说,明朝的整个朝代都贯穿着“教匪”之乱,加之崇祯年间的张献忠之乱也毁坏了巴州太多的古迹。所以元、明两代虽没有能在南龛留下更多痕迹,却恰是对元、明两朝历史的佐证。
在清代,对南龛最有影响力的恐怕要数道光7年的巴州知州陆成本和道光11年的代理州官朱锡毂了。位于神仙坡上端,极其醒目耀眼的七个大字“清江一曲抱邨流”便是出自陆成本之手,仅仅七个字,却包含了四个朝代近千年的南龛情结。宋代的鄱阳人张垓在游南龛时因杜甫的《江村》而作《九日诗》,赞美南龛、思念家乡,其同乡章崇简又步《九日诗》原韵,作《步同乡张垓壁间韵》颂扬杜甫、怀念张垓。到了清代,陆成本便将《江村》和《九日诗》共同的首句“清江一曲抱邨流”以遒劲的笔力刻于崖壁,让后人永远记住了这几人。陆成本本人书法功力极深厚,在巴为官期间颇有建树,他表彰先烈不遗余力,曾主持修缮、修建了汉英惠侯严公(汉代严颜)祠、章怀太子冢、凌云塔等。并将明崇祯年间因镇守巴州城而殉节遇难的知州卢尔惇奉入忠烈祠,在南龛石窟的遗存展区内也保存了他的许多作品;大佛洞下一龛保存完好的《游南龛赋》是清代范嘉乐所作,他以“巴山多奇胜,南龛尤巨擘”赞南龛之奇、以“倘非五丁开,定是巨灵劈”赞造像之妙、以“峡口曲径通,武陵宛咫尺”赞佛地之幽;道光年间,南龛又迎来了一位重史、修史的巴州代理州官朱锡毂,他在处理政事之余,上南龛古寺搜罗逸事,整理巴州的文献资料。在遍观南龛摩崖题刻时,既为部分历代先贤的诗词歌赋题刻保存完好而欣慰,更为太多古迹遭到毁坏而惋惜,于是刻下《朱锡毂题记》,倡议志同道合之士一起保护南龛。两年之后,朱锡毂在泸州知州任上运回的近10万字的《巴州志稿》,成为了巴州最早的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史志,虽在巴为官仅两年时间,却为巴州人民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史料。
在神仙坡崖壁上还留下了一龛民国时期的《游南龛赋》,它是南龛目前为止唯一一龛未遭任何毁坏的题刻。民国时期的巴州知县甘梯云在陪同国军师长田颂尧游南龛登高远眺之际,因感叹南龛的美景和佛像的精美壮观而赋诗。他以“一邱一壑蟠胸久,千佛千龛到眼迷。天谴五丁施斧鑿,风流诸子共攀跻。”形象地描画出了南龛摩崖的造像规模大得令人眼花缭乱、镌刻工艺精美得疑似上天派遣的匠师所造。当面对“杜陵洗墨、严武遗疏”等前人留下的古迹时,又毫不掩饰自己的怀古惜今情怀,由衷发出了“澄清寰宇更何时”的感概。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当时已是86高龄的晚清秀才“孝义郎”刘建功,采用象形写法,巧妙地将“龙虎”二字以上下结构的方式融合成了意义完全相反的“和平”刻于老君洞旁。不仅展现了刘老先生深厚的书法功底,更饱含了老先生一生在尝尽了晚清政治腐败、民国军阀混战之苦后,对中国人民通过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和平生活的珍视!借南龛福地书写“和平”,既表达了希望菩萨能够福佑苍生永享太平的朴素愿望,更是苏区人民对牺牲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巴山儿女的深情祭奠;1992年,甘肃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来巴参观后,对巴中石窟给予了“巴中石窟,国之瑰宝,盛唐彩雕,全国第一”的高度评价。如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志愿在红军中”的张崇鱼先生,为了让世人永远铭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牺牲的四万巴山红军将士、铭记那段与日月同辉的历史,他历尽艰辛、历时19年,又在南龛福地旁建成了“全国第一”的红军石刻碑林,再次拓展了南龛石刻的内涵,它以不同的方式赋予了南龛石刻更加伟大的现实意义。从此,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共同书写着巴州的历史、见证着巴中的发展!
随着巴中统筹城乡、追赶跨越、加快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南龛这个“国之瑰宝”正在逐渐走出大山,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景仰。近年来,我们在越多越多的描写南龛的知名媒体上数次读到了“震撼”二字。的确,站在南龛佛像群下,俨然到了佛国,读南龛摩崖题刻等同于听故事、探历史、学文化。然而,置身红军石刻碑林之中,我们又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看到了信奉了千百年普度众生的佛教信仰的巴山先民的后代,他们通过党的培养和教育,思想和觉悟已得到了不断地的提高和升华,不仅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且最终也会实现和平崛起后的世界大同之梦!这就是南龛石刻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原因,这就是南龛石刻的历史光辉!